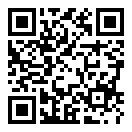从吉隆坡到深圳(连载7)
深圳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但是1990年代中的深圳也确实是千疮百孔的。这是没有矛盾的。不造成矛盾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深圳这十年来确实是进步得比较快;第二,对手更差劲。
不只是深圳,中国这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总体进步还是比较快的。中国高层的战略眼光比起他们东南亚的同僚,明显沉着而有远见。中国186个地级市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中国人的向上和勤奋都是促成这个进步的原因,有赞美并不等于不能发展。
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是不难看到的。1990年代中期,正当朱镕基总理实施宏观调控,控制中国过度的房地产炒作和经济过热时,东南亚小国举国上下却都为炒得正热的“亚洲奇迹”深感骄傲。当中国领导层面对美国的压力,控制外汇的自由流通,他们东南亚的同僚地都在与庞大的国际资金公舞,跟随着跨国的热钱疯狂。当亚洲奇迹变成了亚洲金融风暴,比起其它的亚洲国家,中国的投资优势就明显出众了。
在亚洲金融风暴过后的不景气市场中,马来西亚的本地人宁可搞一些莫名其妙的直销也不愿意干劳力活,工厂、园丘和农场都必须雇佣大量印尼和孟加拉的外来劳工。在88年到96年的景气市场中,马来西亚和其它的四小虎并不能提升工业的技术含量;在景气过去了,它们的人员又不能刻苦耐劳。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上进和勤奋的中国员工难道不是中国或深圳的优势吗?
深圳的另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从中国四处汇集在深圳的富有潜能的年轻科技和技术人员。这个优势加上优惠的投资政策,一些高科技工业的制造厂就开始从台湾、香港、东南亚和欧美逐渐移入深圳扎根。
在十年后的今天,大型的外资企业领导人,都已经看到了中国年轻科技和技术人员庞大的潜能和资源,他们也看到了中国员工的聪明和勤奋。跨国企业在中国已经建立了超过600家研发中心,并且把中国看作它们的世界制造中心。我已经看到中国员工与欧美大企业开始建立了一项在今天的中国最缺乏的东西,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心和信任。
原始积累和诚信
人与人之间的信心或信任在十年前的深圳是不容易看得到的。当时的外资企业以劳力密集的港、台和国内的企业为主,他们并不象欧美大企业那样尊重员工。他们的观念更是非常露骨:“这是原始积累的阶段,我们要完成了原始积累,才有条件谈其它的。”
中国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腾,人们对制度、对社会的信心,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已经隆到了最低点。在这个前提下,再加上老板和领导露骨的原始积累,人的信任度难道不是荡然无存了吗?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非常严重的死结。虽然在高层领导漂亮的宏观布局、中国人向上勤奋的推动和广大市场的带动下,中国在投资发展方面把东南亚国家比下去了,从而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工商界普遍缺乏信任和诚信的行为却是一记要命的败笔。这记败笔造就的是一个内耗很大,非常累人的社会,我的笔记中有以下的记载:
我周边的港资企业老板是以他个人的盈利做为企业的目标的,而员工只是创造的工具而已。这家企业是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老板是在改革开放后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然后再回过头来在深圳设厂的。这家工厂聘请了三千多名员工,生产一些小工业产品。
老板和管理层对自己的地位是非常重视的,最典型的体现管理层特殊阶级的是企业里头的五个饭堂,老板和境外来的高级领导层一个,境外经理和干部一个,国内干部一个,拉长(班组长)一个,最低级的就是员工饭堂。在员工饭堂,我亲眼看到员工自备一个大铁碗排队打饭,打的菜只有一个青菜豆腐而已,就是切切实实的小青菜炒白豆腐,一点也不夸张。
车间的墙壁都利用起来了,除了鲜红的口号,就是写了不少企业的法制。所谓法制就是做错什么就处罚多少钱的条规。
对面做电子玩具工厂的管理也是同一个模子注出来的。工厂的从事部主管告诉我,他们工厂患有乙型肝炎的员工很多,工厂领导视若无睹,任由它传染。
资本积累环境下的前期社会主义实验
就是在这种简直就是前期资本主义的具体环境下,我要在深圳市平湖乡尝试建立一个前期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十年前,谈主义是很敏感的事,在中国谈主义更是敏感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柏林围墙倒塌了以后,即使是对搞社会主义的人来说,社会主义是过时而不是时髦了,是负债而不再是资产了。马来西亚的人社堂在那个时候就改为了人民堂。
在中国,大家从嘴巴到内心,都深信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会捉老鼠的才是好猫。”
我也深信邓小平的这句话,但是我的理解和我中国的同僚所理解的却完全是两回事。我的理解是,不管你谈什么理论,讲什么道理,关键要是可行的,关键要做出来,而且不容许有行为反差。但是我的同僚们的理解则是什么都是假的,赚钱才是真的。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企业能赚钱就是本事,不能赚钱就是狗屁。更重要的是个人要能赚钱,说穿了,到深圳去打工,谁不是要去赚钱的呢?
主义在深圳比在吉隆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肯定是更刺耳的字眼。对主义的理解,我的同僚和我也是迥异的。对我的同僚来说,主义是政治谎言,是虚晃得口号,是过时的概念;现在关键是要赚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