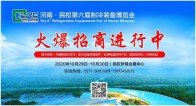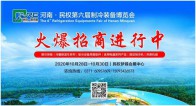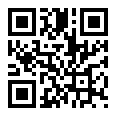热电联产遭遇中国式“冬天”(三)
县城里的琦泉公司之所以日子比省会城市里的银座奥森稍微好过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公司2004年的一次“电力直供”。
按照《电力法》,热电联产企业发的电必须上网销售,而在此过程中,热电企业总是要面对电网公司的垄断压制。琦泉公司的电力直供正是打破了这个多年的规则。
与琦泉公司只有一墙之隔的是齐鲁制药厂的平阴分厂。这家制药厂的年用电量在7000万千瓦左右,以前一直从平阴县供电局买电,电价是0.60元/千瓦时。
2004年初,齐鲁制药厂平阴分厂找到老邻居琦泉公司,与他们商量是否可以实现直接供电,不再通过供电局买电。双方都算了一笔账,如果制药厂从琦泉公司拿到的直供电价是0.50元/千瓦时,制药厂一年节省的电费就达到700多万元;而对于琦泉公司来说,0.50元的电价比卖给供电局的最高电价一度0.43元也要高出7分钱,这样算下来,琦泉公司一年增加的收入也会有400多万元。
双方一拍即合,为了防范政策风险,两家很快签订了一份《联营协议书》,制药厂以现金形式出资307.3万元,占有琦泉公司46%的股份。
2004年5月13日,一场悄悄进行的电力直供行动开始了。董静波带领公司运行检修、行政后勤的30余名员工,与隔壁的制药厂一起,从下午2点至次日凌晨3点,将总长900米,重达10余吨的电缆敷设到位。
随后,琦泉公司向县供电局发了个通告函,告知供电局今后琦泉公司发的电不再上网销售。据说当时供电局大为恼火,立刻对琦泉公司采取了“解网”的惩罚性措施,并到县政府告了琦泉公司的状,指责琦泉公司违反《电力法》。因为《电力法》第25条明确规定:“一个供电营业区内只设一个供电营业机构,供电营业机构持《供电营业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在批准的供电营业区内向用户供电。”
显然,琦泉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电力法》,直到现在董静波对此也没有异议。但他认为,从电是商品的角度看,直接供电是合法的。
他说:“我国现行的《电力法》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其上述规定纯粹带有垄断性质,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家应尽快对以上政策做出修改。”
琦泉公司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最终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供电局做出了让步,承认琦泉热电公司与齐鲁制药厂平阴分厂“由于是联营性质”,所以今后不再追究干涉琦泉公司与制药厂之间的电力直供,但是不允许琦泉公司今后再与其他企业或者终端客户进行“直供”。
“当时把我们逼到绝路了,我们走这一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问题的根本不在地方电力部门身上,而在电力体制上。”董静波说。
据王文华介绍,1990年代初,国家为了支持热电行业,规定的热电上网电价比较高,但电力行业对热电企业并不待见,因为热电的电不如大电厂便宜,所以行业政策总是限制热电的发展,两个行业出现了很多矛盾。
最严重的时候,琦泉公司的上网电费长时间得不到结算,一拖好几个月,最高时拖欠到850万元。这对于当时年销售收入只有2000万元的热电厂来说简直无法忍受。
2001年,平阴热电厂正式改制,更名为济南琦泉热电有限公司,改制当年,公司希望平阴县供电局参股,但供电局拒绝了。
琦泉公司总经理王文华介绍说,2003年,“本着合作的精神”,琦泉再次吸收平阴县供电局掺资入股,这次供电局答应了,正式以46%的股份进入。
但是在将近一年的合作期间,双方在企业共同发展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董事会开不成,在一些项目上通不过,一开会就争吵。”王文华说。
2004年3月,煤炭价格开始上涨,琦泉公司经营面临严峻的形势。就在公司处于生死边缘的时候,县供电局宣布撤资,这对琦泉来说无疑打击沉重。
更令琦泉公司愤懑的是,按照规定,供电局针对热电有一个计划发电指标。一直以来,琦泉公司卖到供电局电网上的电价,计划发电指标内的电价是0.43元/千瓦时,而指标外的电价只有0.28元/千瓦时。
“0.28元的电价连煤钱都不够,而且计划发电指标还占不到公司总发电量的一半。”王文华说。
“给热电企业规定一个计划发电指标显然是不合理的。”王振铭认为,规定计划发电指标的结果只能是热电企业发电越多,赔钱越多。尤其是到冬季热电厂必须要保证供热,超发电量肯定大增,而计划发电指标却并不增加。
其实早在2000年,原国家计委等4部委就联合发布过一个1268号文件,在这份《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规定》中就有明确规定:热电联产可以有效节约能源,改善环境质量,各地区、各部门应给予大力支持。热电厂应根据热负荷的需要,确定最佳运行方案,并以满足热负荷的需要为主要目标。地区电力管理部门在制定热电厂电力调度曲线时,必须充分考虑供热负荷曲线变化和节能因素。
但在强大的部门利益面前,再好的政策和规定都被无形消解了。